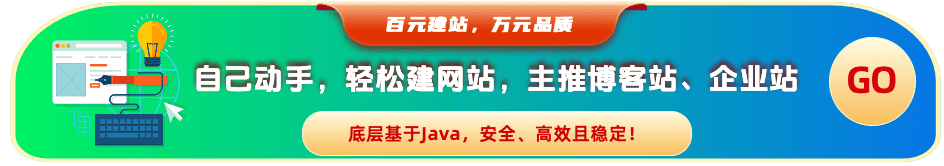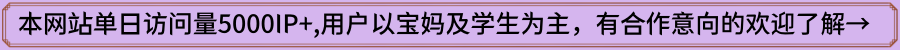父亲的爱
我和爸爸长得很像。我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一把大胡子—他有,我没有。
有种普遍的说法:女孩爱爸爸,男孩爱妈妈。据奶奶说,一岁多时我麻疹没出好,差点要了小命。爸爸接到电报后匆匆从外地赶回来,一进屋,高烧得迷迷糊糊的我马上举起小手扑向他。那时,我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他了。
别人都说没见过这么爱孩子的男人。小时候,他常常把我架在脖子上得意地东游西逛,如展示作品一般。一次正游逛得高兴,旁边有人惊呼:“哎哎,快放下,快把娃放下,娃尿咧!”爸爸躬下身答曰:“不要紧不要紧,等她尿完,等她尿完。”
长大以后,爸爸对我的感情不再溢于言表,像大多数父女一样,我们也是不善于交流,很少坐下来一起谈谈,除非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后来我慢慢体会到那含蓄爱意的真味,那就像是每天萦绕在家中各个角落的饭菜香味,不惊不咋,真实可靠。我是个叛逆过头的孩子,并且继承了爸爸的坏脾气,从小到大小错不断,打错也犯。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无论自己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总会在爸爸的痛骂声中觉得一阵轻松—他一定会在咬牙切齿之中替我把事情解决掉,让我又高高兴兴上学去。
除了画画之外,爸爸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爱种花,不好下棋,更不会打麻将,是个不太能干的爸爸。用妈妈的话说,“连个自行车也不会修”。对吃的喝的更不讲究,有烟有酒足矣。今年出于健康的缘故,爸爸也曾屡次戒烟,并郑重地要求我们监督,可不久即在阳台上被逮个人赃俱获。对酒,爸爸既爱又恨,他的名言是:“酒这东西喝在嘴里就像毒药,难受得很。但是,好就好在喝完之后的感觉。”所以他喝起酒来要求空腹,从不细咂慢品,一二两酒一仰脖便告结束,也不管下肚的是五粮液还是三毛钱的红薯酒。
前两天与朋友闲谈,无意间谈起爸爸,感叹一阵后共同的结论是:性情中人啊。我常常在想,爸爸生来就是为了一件事:画画。看书是为了画画,睡觉也想着画画。他把别人消耗在别处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了。
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对环保问题格外在意起来。他不像人家在公开场合泛泛谈一谈,他完全是一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他会为电视中偶尔播放的一个几秒钟的砍伐森林或挣扎着的浑身沾满原油的海鸟的镜头而咒骂、郁郁不乐上一整天,晚上还要失眠。他更加不能看见人类对动物的杀戮—那足以让他发疯。因此家里连活鱼也不大买了。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家里的爱猫突然病重,不详的预感像魔爪一样撕扯住了一家人的心。连日的四处求医没有什么效果,猫不行了。爸爸固执地仍要带猫看病,我们无声地坐在车上,我看见坐在前排的爸爸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掌抹着泪水。猫在半夜里死了。我因为住在自己的小家,不知道可怜的爸爸妈妈是怎样度过这难挨的黑夜的。为了不让他们更难过,我拼命地忍住眼泪,但又找不出什么更有效的话来安慰蹲在阳台上的爸爸。貌似坚强的爸爸,竟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那两天爸爸不知抽了多少烟,我和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劝阻他。如果抽烟可以令他的痛苦有所减轻的话,那就抽吧。
爸爸老了。以前他会让我给他拔掉几根刚出现的白发,但现在头上的白发已不计其数,不能拔了。
都说淡泊宁静是老年人的最高境界,我看爸爸是难以达到了,虽然他也会偶尔翻一番《易经》、唐诗宋词什么的,可依旧喜怒无常,依旧喜欢喝自来水,依旧在大冬天穿着衬衣饶有兴趣地画着画。
爸爸的心,如同他最喜欢的颜色,永远大红大紫,永远悸动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