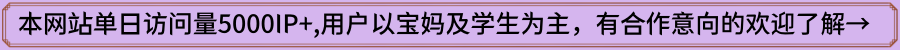鲁迅和思想家_4350字
(一)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0.7冯友兰、0.3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1937年8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
辑》,则发表于1937年3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
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来重温鲁爷的原文。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罗卜青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一段自然是很好的文章,但是细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先生自己,似乎并没有一贯的标准。早年为振奋懦弱的国民,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为此还给汉语增添了一个新词“末人”(与“超人”相对,DerLetzteMensch,直译是“最后的人”)。但在三十年代成为“党的同路人”后,先生致力介绍的却是《铁流》、《毁灭》之类的苏俄革命文学。现在的人,未必会恭维先生的眼光。有人会说,鲁迅在上面的引文里讲的是什么都可以拿,贵到鱼翅毒到鸦片。但是这么一来,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除非你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则,大家(其中也包括许多“末人”)纷纷乱拿之下,你怎么知道他们能够消化?
鲁迅曾经把中国的国民性归纳为“演戏”两字。鲁爷成名后亲见三次反日高潮:东北九一八事变(1931),凇沪一二八抗战(1932),“何梅协定”和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但是先生从未在高潮时写过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倒是毫不客气地讽刺时人的浅薄的爱国热情。什么“当代花木兰”“女子救国”;什么哎呀呀拿起西瓜
吃不下,想想前线将士多辛苦;先生鼻子一哂:你们还是多向敌人学学吧,人家打得赢,“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难道先生指望这些喜欢演戏的汉子,会不把鱼翅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性”,不把鸦片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
甚至六十年后的留学生也进步不了多少。举个最近的例子。据人民日报说,那个在冰上速滑中未判凯西?透纳犯规(撞张艳梅)的荷兰女裁判口出狂言,“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于是一些爱国的好童智争先恐后上中文网怒吼:
“打倒西方帝国主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谁也挡不住!”
不过,鄙人自从三年级时帮助老师处理过几次女孩子间的纠纷后,就知道这种在背后声称别人说了什么的话是最靠不住的。挂着条领带的领队、翻译未必比挂着条红领巾的女孩更纯真,而且双方都使用非母语的英文,更容易产生误解。按常理说,裁判碰到有人抗议,最可能做的事是打打圆场;打圆场时,在这种情况,最可能说的话是就像南茜?凯莉根安慰自己时说的那样“银牌也很好了”。这句话,就足够让心理年龄十三岁的人听成“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何况外事办不成就编洋人的话本是中国官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悠久传统。清朝大臣的奏摺往往和提到的洋码儿原件牛头对不上马嘴;在批判康生的秘密报告中,胡耀邦说他捏造苏共领导对老毛的负面
评价以挑拨两党关系;不久前,鄙人也在网上揭露过最讲究“治学态度”的都人对达赖喇嘛自传的故意误译。真要做事,或者告到奥委会,确实有种族歧视的证据(真有胆量就把双方的英语原话拿出来),以西方现在PC(PoliticalCorrectness)的声势,不怕撤不了那荷兰裁判的职;或者向透纳学习,以后学速滑前,也让运动员练几年花式溜冰,弯道时的小动作也搞得裁判不知电视不觉。当然,这时还能冷静做事的人,是一定要像鲁爷那样,被某些人赠以“卖国贼”的高帽的。
在鲁迅去世六十年后,中国大陆仍然充斥着不知如何做事,却又自以为是个角色的人,他们就像梁羽生笔下的听人传了一句话就要去杀人拼命的傻蛋武侠,被人一煽动就要赤膊做戏,虽说真的让他们在“成人的童话”中露个脸,梁先生还要嫌他们嘴脏。那么,在鲁迅看来正在大量制造“末人”的当时的中国,先生怎么能指望人们会有汉唐时的气魄,“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毫不介怀”?
本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进而比较他人的见解,这使我转向冯友兰和毛泽东。
(三)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但是,他们往往只见殊相不见共相,只讲对立,不讲同一,因此无法突破
东方还是西方的地域界限,或者黄人还是白人的种族界限。
冯友兰在三十年代指出,中西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古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考察文化现象时,科学的方法是从殊相入手,上升到理解它的共相,冯友兰称之为“知类”。这也是老祖宗用的方法。汉代的人谈论金德的文化、木德的文化……说的就是文化的类。中国文化是“中古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而西方近代文化(注意:不是笼统的西方文化而是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文化类型的转换,即成为“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保持着中国特质的殊相。冯友兰是第一个从方法论的高度为中国旧文化的改造指出一条道路的人。
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1941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就内容讲,老毛是信口雌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蛮高明的,中国“新文化”所属的类和它在当前的“特殊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在《矛盾论》里,与冯友兰的雷同之处,还只是隐隐的蛛丝,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是清晰的马迹了。不过,毛泽东是革命家,没
有等待的耐心,对他来说,一个五?四运动,就足够转换文化的类型了。
在指出了改造中国旧文化的道路后,冯友兰进一步考察了这个改造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这导致人们眼界狭隘,“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其中三个是显然的家庭关系,朋友则相当于结义的兄弟关系,臣事君则类似于妇事夫。而西方近代文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即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文化。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家庭,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政治上,这导致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没能走上这条路,关键是中国的思想中缺乏科学,荀子的那种“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驾驭自然的思想,由于秦朝的短命而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要实行文化类型的转换,就要引进科学,发展生产,改革经济,而不在于刻意地“拿来”某一种思想或某一种制度。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缓慢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搞一次运动甚至打拼(台湾网友问大陆人怎么喜欢用“搞”,这里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总结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民族性、科学性后面再加个阶级性,把中国的新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鲁迅是这个新文化的“最英勇
的旗手”。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提倡过什么新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或许和他的学历有关。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卧病生活困难期间,看的是野史和绍兴的乡土文献,直到十八岁进江南水师学堂。他看来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本土的启蒙文化(如敝本家唐甄对专制君权的批判)了解不深,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叛逆因素认识不足。而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则认真读过前辈乡贤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对旧文化中的新萌芽有所认识。老毛愿意承认,“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冯友兰相比,这两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有限。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毛泽东学过斯宾塞的《伦理学》,他们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但是恐怕不知道多少柏拉图和阿奎那,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心理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理学》“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今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妄和八九民运的躁急后,值得重温的,是冯先生的话
:“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毛泽东和鲁迅,就个人才能而言,或许在冯友兰之上;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关键命题的回答,却远逊于冯友兰。哲学使人深刻,信矣哉,信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