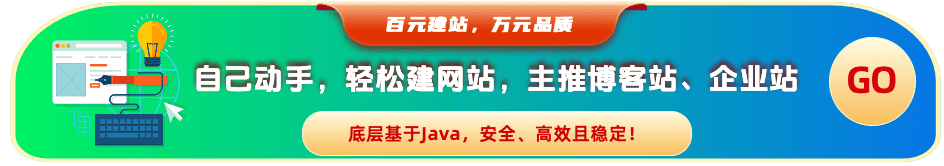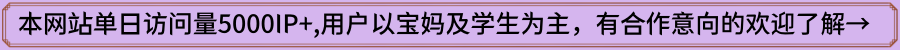写怀——阮籍的孤独_800字
简陋的牛车沿着颠得够呛的石卵路以一种近乎跳跃的步伐前进,路上留下了一直向西延伸的轮印。车上的酒坛跳跃着,挤碰着,破碎着,溅出了辛辣的酒气,溢出浑浊的液体,坛子的碎片崩坏着,碎裂着,对他裸露的手掌手臂作出痛苦的伤害。
前面出现一堵残破的土墙,牛车停了下来。
那跳跃着的血酒与碎坛子也停了下来,血混着酒安静地沿着车板淌在被碾坏的雏菊上。
雏菊被挤压压出了汁水,尽可能地挥发着它应有的清香。一时间,呛人的血腥,辛辣的白酒,雏菊娇嫩的香气---冲击着他的大脑,他意识到没有路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意味着什么。
但对他,对阮籍而言,这意味他又要返回他的住所,司马氏的使者喋喋不休的说教,他不愿意。
他从牛车上翻下身,酒渗入了伤口,使他感到轻微的刺痛,不强的痛楚,但很有效率地咬啮他的肌肉,吞噬他的混沌,揪出他的清醒。
他连翻带爬地登上了破墙,某些个伤口仍在淌血,溶入那一堵墙,污染了那干燥的芬芳,他不在乎,他从破墙上看到将近黄昏的太阳,红彤彤,血一样刺眼,他看自己的手臂手掌,血的回忆被勾起,他痛苦地将脸背过去,再背过去。
嵇康死了,吕安死了,常挟酒来与已尽谈的好友死了;向秀走了,阮咸走了,山涛堕落了,他---阮籍,孤独了。
黄昏的夕阳,没有什么热量,但雏菊的气味---血与酒的气味,再次地浓烈,从新开始,又冲击他的大脑。
喝进的是酒,流出来的是血,流血后饮酒会醉,醉酒的他爱出游,被出游者碾碎的有雏菊---这平时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物到了此情此境竟顺理成章地串联起来,他想起嵇康的诗<<赠秀才入军?其十四>>:“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很讽剌,他想道:嵇康用来与自己谈话的,是头;想出<<广陵散>>的,也是头;被司马氏砍掉的,也是头。没错,就是那颗摇晃的头。砍掉头,也就是把嵇康英伟的身体改短了几寸而已,但这简单的一刀也就断送了一个朋友。司马氏要招揽嵇康,为什么,又要杀了嵇康---
---他害怕,那叫害怕吗?他很快镇静下来,司马氏不知道还可以忍受自己多久,到头来自己的命运会不会像嵇康一样惨淡收场?他愿意死。他愿意到下界陪伴嵇康;他不愿意,他不愿自己的颈脖被肮脏的斩首刀砍断。
此时的他既想哭又想笑---他竟然活在这么矛盾的局面里,但现在他最想一走了之,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他知道,这一去,司马氏的使者,又要在他床前进行又一次的说教,抑或是,在他的柴门外进行又一次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