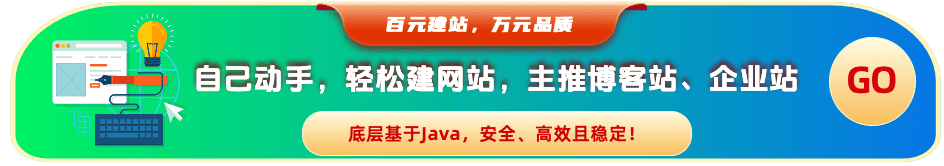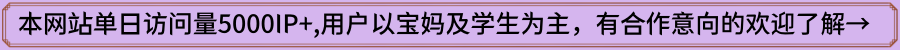锅巴舌尖上的家乡1200字
家乡的上空又该是炊烟袅袅了,这是一年中最馨柔和暖的季节。临近年关,家乡的家家户户拉起风箱烧起大锅,开始蒸过年的馒头了。
每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像一尾幸福的鱼儿游弋在无边的春光里,心若潮起。有风夹着青蓝色的炊烟轻柔地抚摸我,这如约而至的气息,朴素而淡雅。久违的沐浴,驱除了我的风尘,让我幸福如水。
看见炊烟,使我想到儿时倚门唤我回家的母亲。离家的时候,我不敢回首,我怕有关炊烟的往事锁住我欲飞的翅膀。这些年行走在炊烟的牵扯里,除了母亲,谁又能把它拧成一股时时牵动我心帆的缆绳呢?炊烟在我所居的那个城市已经灭绝了。找它,只有在梦中,在童年的记忆里。长久置身于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中,我常常迷失了自己。只有在家乡那袅娜地上升的炊烟,那一声长、一声短的响彻整个村庄的呼唤,才能帮我找回真实的感觉。那一缕缕炊烟,那一声声呼唤,属于我,属于我的童年,是我记忆和梦境最鲜活的一部分。炊烟连结着我和母亲,也寄托着我对爷爷的思念。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逝了,他留给我的记忆是模糊的,惟有与炊烟联系起来才清晰可闻。爷爷是一个木匠,大名陈广居,人称陈木匠,远近闻名,不是因为他像李春那样设计修建了赵州桥,而是他将手中的那把斧子抡得飞转,挥舞出一个儿子上大学。多少年后,家乡人口普查,全乡只有一户人家的子弟在外面读大学,那就是父亲。那个贫穷饥饿的年代,要供成一个大学生,其艰难可想而知。
爷爷没日没夜的劳作,手累假了,落了个半身不遂。他一生打造过无数的家具和棺材,最后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把椅子。以后的岁月里,椅子成为爷爷人生的主要道具,每天他全靠那把椅子挪动自己。
姐姐想起的是爷爷宽宽的背:在劳动之余,爷爷总爱背着姐姐四处走动,用他那粗粗的胡须轻扎姐姐稚嫩的小脸;哥哥想起的是爷爷做的木童车:坐在童车上由爷爷推着,嘟嘟嘎,嘟嘟嘎地跑动;我呢?我能想起的便是那炊烟飘过屋顶之后,爷爷手中的那块锅巴了!
吃饭的时候,爷爷面前有一个碟子,专属于他。那碟子很小,那是母亲特备给爷爷的精肴:一块白面锅巴,几粒酱豆,有时还有辣椒。我和小哥哥的眼睛,不免被那锅巴馋住,爷爷也总是慈爱地给孙儿撕下块块锅巴。眼见爷爷手中的锅巴已是“多乎哉,不多也”,而我们却还是巴巴地望着,又害怕母亲责备的眼神。时至今日,难禁内疚:老人的慈爱、小孩的馋,是如此地剥蚀了爷爷本已菲薄的晚年待遇。
后来我有了工作,遍尝人间美味,可总也嚼不出生活的原汁原味。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清晨去上班的路上,又看到了久违的锅巴。以后便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清晨上班都会在青峰的地摊上要上一个锅巴,蘸上酱豆,抹上辣椒,饱尝这一份生活的甜香。
清晨凉凉的风里,这个相伴良久失而复得的锅巴使我真实地感到与家乡紧紧贴在一起。这最地道的味道,便是我贫困的童年、火热的家乡之味啊!欣喜的是现在的孩子不用盯着老人手中的锅巴嘴馋,他们在遍尝各种美味之后不屑于这不起眼的锅巴。而在异地他乡,最能勾我心魂的还是那袅袅的炊烟,那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带焦的锅巴。
--老板,请多放些辣椒,让我在洒满阳光的土地上,辣出眼泪,品尝生活中那些真实而又辛辣的部分,不至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