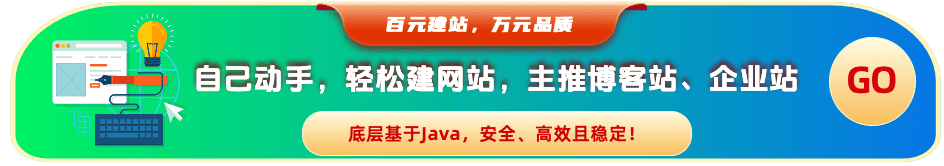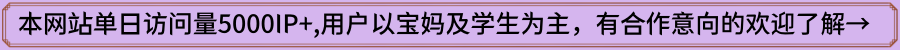媚姨_3750字
光州的茶楼,总是有异常热闹的早晨,在这人群如此密集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琐碎而新鲜的故事在这里衍生,有的很快就终止了,有的则不停地延续着。我们一家和媚姨就是在这里相识的。也许,我该用“相遇”,因为我们共处的时间实在太短,我并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足以去“认识”一个人,但若只建立一种整体的感知,时间就显得相当充裕了。在茶楼里的交谈,媚姨一直是主角,她满怀自豪且略带傲气地描述了自己毅然抛弃“铁饭碗”,冒着巨大风险下海经商的工作经历,媚姨是那种广义上的成功女人——年近五十却保养得当的皮肤,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高档的名牌衣衫,还有那些价格不菲的首饰,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然而,她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已单身多年的她在初识的我们面前毫不忌讳这一点——这便使我感受到一种被信赖的感动,轻微而奇妙,尽管我仅仅是她和父母间交谈的一个旁听者。几十年孤家寡人在商海打滚,媚姨有着太多对我来说奇特而遥不可及的经历。不仅如此,我惊异于父母对媚姨谈起的他们自己的创业经历,这些从来不曾对我提及,大概媚姨也不会对她的孩子说这些吧。也许大人们总是认为,那些曾经加附在自己身上的苦难和艰辛,不应在孩子单纯的心灵上烙上印记。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无知与天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深深地忏悔,为我对父母的过去的无知,为我对生活所赋予的一切的无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话题很自然的转移到我的身上。媚姨一直不停的夸我文静,说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乖的孩子,而当她得知我就读于时,重点中学时,更是毫不掩饰她的赞赏之情——我相信她的称赞是发自内心的,我并不是自负,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无缘无故很讨长辈喜爱的孩子——这也许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优点。然而我却时常为之担忧,我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暗示着我有自己所不能察觉却时刻笼罩着整个意识的那种虚伪性——目睹过我与父母的激烈争执的人,大概都会产生这种怀疑。我并不足够真实,这一点是很肯定的,我能让一个极度厌恶的人相信我爱他,而有时,又会使真正爱我的人以为我背叛他。当然,对于前者,我比较得心应手,或者说每一个人都会比较得心应手,因为这似乎成为了在这世界生存所必须的手段,周围所有的人,身边所有的事。无一不在暗中督促着你对这一能力的不断提高,生活围绕着这个主题严格的锻炼着我们。而后者则是这一现象的必然产物。那一天喝完茶后,我刚好要上钢琴课,而刚好公司已托付给一个可信赖的人的媚姨正好闲得慌有意要学钢琴,我提议媚姨搭我们的车一同去琴校看看。媚姨说她也有车,只是儿子工作后就给他用了,她说先问问她儿子有没有空送她去。于是我们互留了电话就各自回家准备了。回到家换好衣服、带上课本,我在出门前决定给媚姨打个电话,我想她儿子一定“没空”的,因为我可以从媚姨的话中听出隐隐约约的无奈,里面还搀杂着某些期待——我这方面的感觉一向异常灵敏。接电话的是媚姨的儿子,声音有点慵懒,可能刚睡醒不久,我下意识地瞟了一下壁钟,时针直愣愣地挺在10和11之间。媚姨接过电话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她儿子刚好一会有事,她可能还是得麻烦一下我们。我故意忽略了这个无奈却决无恶意的谎言,心里有些沉重却故作轻松地与媚姨约定在茶楼前等她。在爸爸的车上,前排的右座是我一贯的座位。理所当然地,我第一个看到了从车右边出来的媚姨,可我几乎没有认出来——不见太阳的初冬上午,气温不算低,却刮着一阵阵的风,媚姨加了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紧紧的裹着身体,有些艰难的快步向我们的车子走来,我发现媚姨原来很矮很瘦。上了车以后,媚姨很自责地对让我们表示歉意,同时也可看出她有难以掩饰的兴奋。我回头看着后座笑容满面的媚姨,发现她原本齐整的发髻被风吹得有些杂乱,而没有了茶楼通明的灯光的照耀,媚姨脸上被岁月刻上的细纹也失去了掩护——媚姨在我眼中骤然苍老。我有些不忍地扭过头将目光投向窗外,媚姨那也许现在又“回归”被窝的儿子曾注意到他母亲的这些变化吗?——我痛苦地思索着。后座的媚姨和妈妈又很自然的交谈起来,其实说是妈妈在听媚姨倾诉应该更为恰当,很显然媚姨有着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孤独,她迫切的需要一个倾听者,需要一个愿意和她一同分享或是分担这些往事的人。我依然是一个安静的旁听者,对于媚姨,我有太多的好奇,而由此而生的许多疑惑,只能想却不能问,我希望从她们的对话的蛛丝马迹中寻索答案——媚姨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为了离开那个被她称之为“废物”的男人,她放弃了除了孩子以外的一切。之后不久,她又顶着几乎是所有亲友的反对辞掉了稳定却清贫的工作,一个弱质女流孤身下海、白手起家,为的就是要给儿子“高人一等”的生活——无论如何,她做到了,她用近百万将儿子从重点小学一直买到重点高中,用金项链换来了老师对其儿子的“照顾”;她儿子的生活学习娱乐用品一应俱全,日常开销更是大得惊人……而她那由外婆一手带大的儿子却一直怨恨着她,因为她在他最需要母爱的时候她永远都不会出现,她在他眼中只是一部工作机器——“他有时甚至不愿叫我妈妈……”,媚姨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没有作出任何反映,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想我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分担媚姨的悲伤,这种想法也许过于自私,然而每一个在尘世挣扎的人,都会有只属于他自己的无奈和痛苦,我也有我的,所以我们必须学着自己去承受。我在倒后镜中窥视到了媚姨朦胧的眼睛,泪水是一样不错的东西,尤其是在伤感的时候,尽管它并不能抚平伤痛,但多少都会带来一点温柔的慰籍。我感谢每一个曾在我面前流泪的人,因为在那一刻,他们对我毫无戒备、完全信任——这是授予我的无上的荣幸!媚姨在同一天第二次让我感动……手机尖锐的铃声打碎了有些凝固的空气,媚姨几乎是在按下接听键的同时恢复了常态——目光锐利、语气果断——散发出典型女强人的气质,又是一种骤然间的变化,我的心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许多刚才已被歼灭的疑惑又疯狂的重生……
我们到达琴校的时候已是正午,天气却越发的阴暗了,想必一场大雨在所难免。媚姨一下车就马上缩着身子裹上了大衣——其实那天真的不冷。我上课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对媚姨说妈妈可以带她到秘书那里咨询一下,她也可以自己看看简章,我得去上课了。媚姨很和蔼的笑着点了点头,摸出了口袋里的老花镜带上,仰头看起墙上的简章来。我匆匆走进琴房。我的老师——同时也是这间钢琴学校的校长,轻声的问我:“那个老婆婆是谁啊?”老婆婆?——我的心忽然一颤,好象有什么东西在迅速下坠,透过虚掩着的门缝,我看到了那微曲的背影、有些零乱的发髻、缩卷的双臂,还有那副刺眼的老花镜——我急切的想反驳什么,但是我分明感觉到了语言在现实的面前是多么的空洞和无力。我只能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与媚姨别离时已近傍晚,空气里果然穿插起点点雨丝。爸爸妈妈将我和媚姨送到了我们所住的小区路旁,就急着外出办事去了——我明白他们苦于在矛盾中寻求平衡,我觉得自己今天得到的陪伴有些奢侈。走在回各自的家都必经的那一小段路上,媚姨依然是优秀的演说者,我则是天才的听众。我们在这种奇特的交流中各自满足,并且都异常清楚这不过是最后的告别仪式。我随着媚姨的步伐在一间新开张的快餐店门前停下,虽然这间店子就开在我家附近,并且生意异常红火,我却本能地抗拒去光顾——我无法接受现在几乎所有都市人为了节省时间的这种生存方式,我一直固执地相信,时间应该是给生命以自由的使者,而非将灵魂套上桎梏的魔鬼。当时间仅仅作为时间本身而被珍重时,我不明白人生还有何意义和乐趣,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还能在这虚空无聊的域界马不停蹄地前行,也许那是因为前方缥缈模糊的希望总是让人感到近得触手可及吧,而有时侯疲惫的心会将这朦胧的希望形式幻化成一个小小的质点——媚姨面前的我,大概就是其一吧。媚姨很认真地指了指快餐店前马路对面一大排住宅大门中的一个,告诉我她就住在那栋的某一层,确切的数字我忘了,或者也可以说我从来都没有记得过,因为我知道那对我毫无意义,我想我和媚姨只是两条孤独的延伸的直线,注定了只能有一个交点而已……隔着马路,凝视着隐去媚姨瘦小身影的那道大门,我品味着媚姨临走前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的感觉,那是一双烙满了生活茧记的手,它印记着一个成功的女人不为人知的辛酸过往,我没有经历过,却由于这十几秒的接触,似乎有了某种深刻的感触。淡然一笑,收回目光,我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正式将这段奇遇归化成回忆……评语:“有时,你和他是朋友,有时,你和他是“敌人”;有时,你和他是知心人,有时,你和他是“陌生人”;有时,你找寻他,有时,你躲避他……你同你的父母、老师、长辈,甚或其他人之间,是否拥有过如此众多复杂、微妙的情怀?”——在今天越来越丰富与热闹的现实生活中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纯粹的关系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微妙?为了表现这种微妙关系作者选取了“媚姨”这样一个看似与自己萍水相逢实为自己所深深了解并深有感触的人物。媚姨的故事是文章的明线。文中的媚姨看似一个成功的女强人——干练、健谈、满面春风。然而作者总能在满面春风的媚姨身上找到种种不春风的细节——媚姨近乎神经质的倾诉欲、媚姨一直掩饰的与儿子之间的尴尬、媚姨在寒风中凸现的并不年轻的外貌——这些细节反映着一个共同的事实:媚姨丰富的物质生活背后、女强人的外表底下更多的是生活中缺乏他人关爱的精神生活方面的脆弱与悲哀。“我”与父母的故事在文中是若隐若现然而并行不悖的暗线。作者总是在观察媚姨、发现媚姨、认识媚姨、特别是侧面表现媚姨与其儿子之间的关系时顺带地“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并不时地反省自己对父母的忽视以及对自己拥有如此父母的庆幸。正是这种庆幸让读者沉重的心中有了一丝暖意。
文章的叙述看似琐碎实则明暗交织有条不紊。而叙事中的细节描写更为凸现人物形象与文章主题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文章的一大亮点。(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