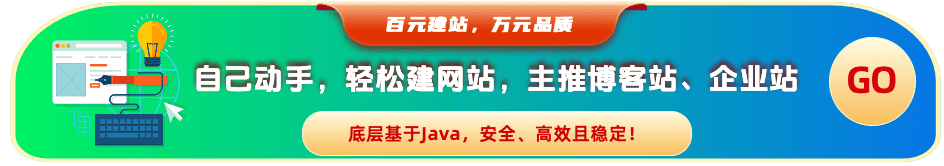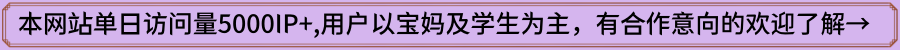瞳冬
【就像映在你瞳孔里的那一抹冬天】
哪一个人能没有几个秘密?它们或许承载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或许烙印着那些曾让人窒息的疼痛,但无论怎样,它们都会被埋在心底,用最柔软的记忆包裹,小心翼翼地封存,即使在时间的长河里泅渡,即使经过了好多次的飞沙走石,它们都还好端端地躺在那里,散发着久远的光亮,但那份怅然若失的无奈,就像埋下一颗明知不会发芽的种子;就像用心去叙写一个明知不会存在的故事;就像一直在费力地挽留、想念、找寻——那个明知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你。
与你相识有多么久?我坐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扳着手指细细地数。初次相遇的那一天,是明晃晃的盛夏,我们的小镇上道路两旁都种着高大的梧桐,那些抖动的叶子把直射的阳光筛成零零碎碎的光斑,然后把我们温柔地包裹。那时候的我,还是穿着背心短裤,一放学就扯起书包狂奔,然后在路上一边叼着快要融化的冰棒一边单手扶着车把横冲直撞猛骑的初一小女生。没什么心机,没什么城府,生活就像一条一次函数的直线一样简单明快地向上攀爬。就是那一天下午,天出奇地闷热,我热得垮着肩膀,握着手里汗津津皱巴巴的一元纸币走进便利店,叼着冰棒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坐在台阶上的你。你穿着漂亮的格子裙,扎着辫子,皮肤白得透明,却异常的瘦,在台阶上小小地缩成一团发呆,显得过分伶仃。
出于好奇,也出于对你莫名的怜悯,我在你身边坐了下来。你怯生生地往后缩了缩,直起了脊背瞪着我,眼里写满了防备。我笑了,你就像猫一样警惕。很想满足一下当姐姐的膨胀的虚荣心,于是抬手想摸你的头,可你却躲开了,仍然警惕地瞪着我。我起身进店又买了一根冰棒塞到你手上,你果然还是天真的小孩子模样,犹犹豫豫地接过,看着我,但瞳仁里的敌意却终是褪去了许多。
你开始说话,声音过分地纤细。你说你害怕爸爸妈妈吵架,所以跑了出来。你说着说着就拉下了嘴角,你抬起细弱的胳膊比划着,带着哭腔说你家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的屋子,你的房间里有很多洋娃娃,但你的父母却不常回家,只有阿姨定时来打扫做饭。大门一直沉重地关闭着,房子里一尘不染却总是冷冷的。偶尔你的父母回家,却不曾抱你疼你,只是简单关心几句。而他们彼此却不知有多大的冤仇,一不投机便歇斯底里地大吵,东西摔到光洁的木地板上便是久久回荡在空旷的房间里的闷响。有时吵完二人便分道扬镳,从不曾记得还有一个吓得瑟瑟发抖的你。你小声地哭着,细细的眉眼间全是抹不去的恐惧和委屈。你的眼泪落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就马上蒸干消失,来不及晕染成深颜色的圆。
同样不谙世事的我看到这样的你,早已乱了阵脚,不过维持着表面的镇定,轻拍着你骨骼突兀的背脊。你哭累了,低着头小声地哭泣,奶油冰棒早已融化得一片狼藉,摊在地上像一张丑陋的脸。
——当时的你,莫名地让人心疼。就像是白色的风信子没有勇气舒展,于是安静而脆弱,没有任何防备地展开充满苦痛的皱褶的心。
那天下午把你送回家,站在豪华的大门口你显得那么渺小。你轻轻地拉着我的手不说话,眸子里却写满了乞求。可天色已经昏暗,回家迟了也是要挨训的,于是只好狠心掰开你的手,给你留下我的住址便先走了。
——那一天的天很灰,沉沉地向下坠着。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事物都会一直是它应有的颜色,一直以为所谓的生活都会像我所想的那样快乐。风淡淡地,不急不缓地一直在吹,把生活表面的云淡风轻缓慢地,却坚定而又毫不犹豫地慢慢拨开,露出复杂的内核。街边的路灯已经渐次亮起,拓印出我的影子伸长又缩短,缩短又伸长。其实我们都还小还软弱,没有刀枪不入的保护膜。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正面对着书桌发呆,听到有轻轻敲窗户的声音。起身拉开窗帘一看,你站在窗户底下,抬起头看着我,眸子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像极了什么幼小又神采奕奕的动物。开门出去,你靠过来倚在我身边,犹疑着扯住我的食指。
你总是像只小动物,动作总是迟疑轻慢的,像受了什么惊吓,又总是喜欢依在人身边,缺失安全感般地想寻求些微的温暖。
和你在花坛边坐下。夏天的晚上,风有些许的凉,蝉鸣已经渐次地息了下去,叶子上也挂上晶莹的露珠,花丛中间或响起几声虫鸣,除此之外便是静谧漆黑的夜。
你不说话,只是抬着头用夜一样黑的瞳仁注视着我。你的皮肤在黑夜的映衬下越发地亮,甚至散发出微微的光。沉默了一会儿,你拉着我的手往前走,说要带我去你的家。你精灵一般在前方悄无声息跳跃地走着,把我带到那个树丛掩映中的富人别墅区。
你掏出钥匙开锁,然后费力地推开那扇对你来说过于沉重的大门。你的家很大,但过分地空旷,沙发暗色的影子在客厅中央静默着,落地窗完整地勾勒出窗外的夜景。那些树叶被风一吹无声地摇晃,像极了鬼魅的影。你打开灯,我看到客厅墙上你们的全家福,你抱着绒毛熊穿着红裙子站在中间笑得很明亮,而你的父母拘谨地坐在两旁,他们年轻的面孔精致又骄傲。
你拉着我盘腿坐在地板中央,像两只被关在城堡里的鸟。我抬起头看着高高的华美的穹顶,我的家和这里那么不一样,它狭小却温暖,被暖黄色灯光和饭菜的香味笼罩,欢声笑语可以溢满整个房间。而这里的空气弥漫着凄冷的味道,所有的家具都闪闪发亮地安静地呆在那里,所有的室内植物都不紧不慢地细声呼吸,你所有的绒毛熊——它们不会陪你说话,只会瞪着黑亮的眼睛沉静地望着你。
你只是一言不发地紧紧贴着我。我知道你是想多汲取一些爱和温暖,哪怕只有一点一滴。你小小的脸在水晶灯的照耀下有些病态的苍白,瘦弱的胸腔随着呼吸轻轻地起伏。你闭着眼,睫毛微微地抖动。
——你是太天真,还是太痛苦,为何会毫无防备地选择依赖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而我同样幼嫩的双手又能给得了你什么。可是此刻,我却宁愿用单薄的肩膀环绕住你,和你一同起伏着呼吸,如果这黑夜太过漫长,我会用我的微笑来帮你点亮。
就从那一晚开始,我们变得异常熟络,你也渐渐褪去你犹疑的外壳,露出孩子天真的模样。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花,便总要扯着我跑进市里大大小小的花店,穿着公主裙在那些花丛中翩跹。花店里的玫瑰开得艳,你抖动着睫毛,微闭上眼轻嗅,因为喜悦而红润起来的脸颊甚至击败了玫瑰的娇。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抱着绒毛熊对我笑的样子,微微的粉红从你洁白的皮肤下透射出来,再通过你的笑容蔓延到整个脸颊,如一树春开便染了一林的艳。
但你总还是会在不经意间慌乱,不经意间忧郁静默,你总还是会排斥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城堡。也许你向来习惯静默地隐忍,所以你不会说出来,只是拉着我的手低着头,用孩童的方式作无声的抗争。有时拗你不过,便把你领回家中吃晚饭,说是经常一起玩的妹妹。妈妈见了你便十分喜欢,连声说你太瘦了需要增加营养,手忙脚乱地张罗菜色。你坐惯了一个人的长餐桌,用惯了一人量的大餐盘,从来都是一个人低头沉默地吃饭,看到这被暖黄灯光笼罩下一大桌的五颜六色,有些许的受宠若惊和不自在,于是站在我身侧,拘谨地扯着我。妈妈笑着把你搂过去,不停地给你夹菜,很快你面前的碗里便堆得山一般。你拿着木筷拨拉碗里的菜,小口地挑起米饭。但不一会儿便渐渐地笑逐颜开,嘴角沾了米粒也顾不得擦。
有时候,你会在家里留宿。黑暗寂静的房间里,我们总会小声说话到凌晨。你紧紧地贴着我,我感受到你薄凉的皮肤渐渐变得温热,你轻轻地说要是我是你的亲姐姐该多好,之后相拥沉沉睡去,一夜安好。
——岁月的锦缎上会有多少抹难忘的亮,当时光无声地匆匆交错,于是我们的生命相互套叠,让我接近你,让我看到你的痛,让我见证你困难的、歪歪斜斜的又执拗的成长,让我陪伴着你,让你从苦痛中逃离些许,让你可以尽可能多地绽放笑容。而你我只是孩子,无法操控命运的转轮转出我们希望的轮回,多少日夜过去,我们还是天地间渺小的一粟,还是让最平常不过的喜怒哀乐牵动着我们的心。但有那么一种情感在暗暗地抽丝,慢慢地生长,紧紧地扼住我们的心。我们如同亲姐妹一样,能够看到你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然而我却忘记了,在你的家中,两个人的战争还在日复一日地继续。裂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并悄悄地蔓延,直到最后分崩离析了曾经那么欢喜地构建起的世界。那一天,你颓然地来找我,早已没有了初遇时慌乱无助的样子,但淡淡悲伤的表情,依旧在你的脸上蔓延。其实我知道,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地共同掩饰着这一切,有一些伤痛终究无法掩埋。
夕阳给你的头发披上了金灿灿的颜色,模糊了你的轮廓。依稀看着你嘴角下拉,如负气的孩童一样走过来。我知道,他们常年的争吵已经让你麻木,你一直流连贪恋于外面的世界,如同贪玩的鸟儿总忘了归巢。你以为争吵就会这么一直继续下去,起码以后你努力,你靠着好的家世可以远走高飞,但你的父母是怎样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让这根深埋的导火索慢慢地显露出来,然后毅然决然地丢弃往日一切的根基,头也不回地做回陌路人。我知道,不管曾经作过多少的铺垫和猜想,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仍让你措手不及。
你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无助哭泣,但仍改不了的习惯是依着我。于是你一言不发地轻轻捏着我的手,如几年前在那个静谧的夜晚一样,一步步慢慢地走。在那时,你领我走进的是个华美但死寂的牢,而现在,它对你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你轻轻推开那扇门,眼眶微微地泛着红。你父母那张桃木雕的大床还安静地呆在那里,散发着熟悉温厚的味道,不知道它的主人已经分离。你轻轻抚着床边的大衣柜,一个个拉开那些抽屉,原来那些熨得平整的衬衫,干净的领带,笔挺的长裤都不见了,只留下空空的抽屉底,那些木板的断茬还泛着白剌剌的光。卫生间里的漱具,鞋柜里的鞋子也都少了一半,这个房间连和平温馨的表象也维持不下去了,如同原本安上的假肢被残酷地卸下,血肉模糊的伤口阴惨地暴露在空气里。
你转过身来抱住我,终于小声地哭了起来。
从那一天开始,你真的开始独立了。你母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你把保姆也辞去,决心一切都由自己料理。我担心你在深夜一个人蜷缩着哭泣,好几次前往陪你,但你却用沉默和微笑婉拒。你是下了怎样的决心,忍着怎样的痛从柔弱的外壳中破茧而出。你开始变得凌厉,变得倔强,但又越发地沉默。似乎是因了苦痛的根源被一刀切断,你可以清净着一个人,而不用忍受来自争吵的源源不断的折磨,你变得神清气爽了很多。
那一年你16岁,在绽放的花季,被迫成长被迫坚强。
你对我说,你在筹划一场旅行,一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你在说这些的时候,漆黑的瞳孔闪闪发亮。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结伴出游,去厦门。你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长长的头发扎起来,挽着我的手兴高采烈地一路都在说。飞机颠簸着穿越云层的时候,你终于累了倦了,靠在我肩膀上闭了眼均匀地呼吸。看着你渐渐发育出棱角轮廓的脸,看着你恬静的睡容,我的心里是层层叠叠的隐痛。我知道你快要离我而去了。你一定有了勇气去承受更多的伤痛,用你的隐忍把它们消磨或者用你的棱角把它们刺破。你是雄鹰,经受了这么多的锤炼,本应飞向更远的苍穹。
厦门的天气是朗朗的晴,天空干净并且蓝得透明。你不打伞,勇敢地把皮肤暴露在七月的骄阳下,要染上健康的棕。我们经过厦门大学,沿着马路一道走的时候,人已经变得稀少,我们走到演武大桥边,顺着栏杆走到桥底下。
这里不是观光区,只有几根桥柱伫立在海水中静默。你脱了鞋,光着脚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勇敢地挑战细沙灼人的热度。海水泛着白沫,一排排翻滚成暗色浪涌,沙滩上有海水冲刷过的暗色痕迹,边缘勾出不规则的弧。
海滩太荒凉,只有潮汐撞击海岸的声音,反反复复执着地回响。你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一步步向着海水走去。海水漫过你的脚踝,携卷着树叶树枝残损的海藻一次一次翻涌过来。我看着你把小腿埋在不断高高低低起伏撞击的海浪里面,发丝被风高高地扬起,思绪有一霎那的放空,而后拿起相机,轻轻按下了快门。
我只是想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从现在开始。
烈日炎炎的中午,我们大汗淋漓地骑着双人自行车。厦门的路有弯道有起伏,我们时而奋力蹬车却还是如老妪般踉跄,时而停止蹬车张开双臂享受下坡时铺面而来的凉风。我们经过了好几个海滩公园,趴在栏杆上看那些凶猛的海水用力冲过来,冲过来,撞击桥柱,溅起无数珍珠。你在扑面而来的湿润的水汽中痴迷地闭上了眼,侧脸上氤氲着娇艳的粉红。你说你向往汹涌的大海,仿佛置身在无边无际的自由。你说你喜欢这里长长的起伏的像是没有尽头的路,好像充满希望地一直走,一直走,越过坎坷穿过困难,就能到达那个希冀的发光的未来。
入夜,我疲惫地躺在旅馆的床上,而你像慵懒的猫伸个懒腰,在黑暗中轻笑。我问你怎么了,你裹着毯子翻身爬起,声音中填满了期待。你动了出国的念头,你说你爱上了伦敦阴晴不定的天,爱上了淡淡忧郁的终年不散的雾,爱上了大笨钟浑厚悠远的响。你拧亮台灯的开关,在暖黄的灯光下瞳仁闪闪发亮。我沉默,我知道这一天终是要到来。你有好的家境,又没有什么羁绊,自然该出去闯一闯。你说这个想法从父母离婚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你想要的是没有烦恼的一个人的生活,你要的是纯粹的自由。你说想要在那里找一间大学,每天在校园里抱着书本静心地散步,听塔顶上的白鸽唱歌。之后你可以去旅游,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普罗旺斯的花海,比如墨尔本的阳光。你接着又蹭到我身边,皱起可爱鼻纹,抱着我的胳膊撒娇:“我不会忘了你的,啊?”
我知道你在太深重的疼痛下被压抑,想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阳光,但你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阅历,想象都太过美好。但我想你其实早已下了决定,决心一个人承受路上所有的艰难与苦痛,征询我的意见只是敷衍。我也知道我不能一直陪你下去,我过的是紧张的高中生活,我面对的是高考。我还能说什么?我不是你的谁,怎能擅自替你决定什么。我只盼望你能如你所说,不要忘了我。
从厦门回来之后,我闲在家中日复一日百无聊赖地看书,消磨掉无所事事的假期。而你开始生龙活虎地四处跑着打理出国的事情,只是在晚上回家之后与我电话交谈。你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一天比一天更多了几分兴奋的不安分的躁动。临别在即,我所能回应的,也不过只是泛泛的“一路平安”。
……
你走的那一天是深冬,天空中正纷纷扬扬地下着雪。你越来越青春,越来越挺拔,即使仍然消瘦,也不再是以前柔柔弱弱的样子。铺天盖地的白,而你穿着火红的羽绒服,淋漓地站在这铺天盖地的白里,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烈火。你戴着厚厚的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亮亮的眼睛。你的瞳孔里映着大片大片斑驳的白色,你冲着我微笑,眼睛细细地眯起来。我冲你招手,我说快走吧,晚了就赶不上车了。你要坐火车去北京,然后从北京飞英国。
车开动了,你的脸贴着车窗冲我招手。我脑海里开始浮现与你在一起的一帧一帧的画面,记得你黑亮的眼睛,记得你哭泣的表情。那些画面被放得越来越连贯,你的每一个表情都飞快地从我眼前掠过,悲伤的欢乐的,坚定的犹疑的,从久远的朦胧过渡到当下的清晰,像是刹那间你便长大,便远行,便离我而去。我不自觉地开始跟着火车奔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直到摔倒在茫茫的雪地里。
你走之后一直杳无音信,留给我的最后记忆便是那片白茫茫的冬天,它越来越模糊,如你渐行渐远,最后化成丝般缱绻的想念。我有时会想象,你是不是在异国执着地追求梦想;你是不是去过了那些你爱的地方,你有没有遭遇美好的爱情,而后义无反顾地陷入飞蛾扑火的狂热。我知道,这是一场测不到距离的远行,你的梦已经太远,你的翅膀已经太大太宽,你渴望飞,渴望飞遍整个世界。有时会做关于你的梦,每每从梦里挣扎着醒来,都似乎还能用指尖触摸到你脸颊的温度,而那在脑海中存在着的笑容,却不过只是虚无。我想,你是否还记得,在天的远方,海的彼岸有一个我,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曾经与你同样稚嫩又青涩、而如今却一人独自怀念着的我,你是否还记得——
某一天,有信寄到家里来,信封上是从未见过的地址。当下心里的兴奋开始压抑不住地突突地膨胀,我拆信的指尖都在颤抖。一定是你。拆开来掉出的果然是你的照片。你站在伦敦的冬天里笑得灿烂,你的瞳孔倒映着冬天,又盛满足够融化一整个冬天的骄人的阳光。照片背面是你临走时,我送你的那首诗——
当你为了梦想
独自一人去往远方
开始一场
名叫坚毅的关于拼搏的流浪
当你为了梦想
独自一人去往远方
我们站在空旷的飞机场
用酌酌真情把你的航班仰望
一万米平流层稀薄的空气
托起你的梦想
阳光穿透云层
青春的心闪闪发亮
旅途的颠簸
抵不过那些切切的希望
当你飞越茫茫的大洋
海浪漫漫地翻滚
当你走下飞机
踏在异国的土地上
当环绕四周陌生的面孔逐渐变得熟稔
当黑色的瞳孔逐渐适应异国的阳光
你是否还在坚持最初的梦想
你是否还会把祖国的烙印牢牢刻在心上
当你独自一人走在落雪的街道
当伦敦的大雾把你的轮廓笼罩
你是否还能想起
遥远的北方
鲜明的四季
和四季里永远微笑着的我们
你是否还能回忆
那些哭过笑过闹过的时光
即使它们已经泛黄已经远去
当你在异国的故事里
执拗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不要忘记你承载的
是所有爱你的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