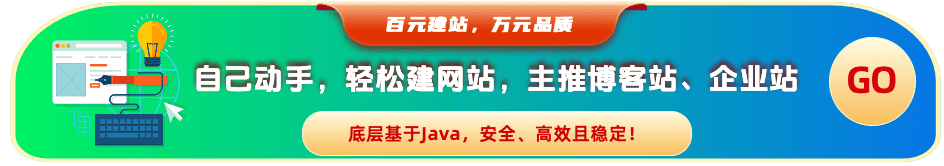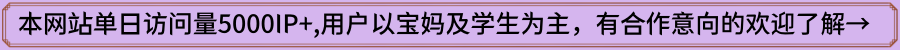舞殇_2150字
第一次见那个女孩是在学校的舞蹈厅。
星期六清晨,我总是很早就到排练厅,等人渐渐多了,然后开始练习。
大概是正在把杆上压腿,突然有个女孩子推门进来,她显得很急,一直喘着气,她褪了鞋,对正看向她的形体老师说了一声报告,便进来,换了白色的舞鞋。
她走过来时,我看清了她的样子。
清瘦修长的身材,一张略小的细致的脸,及紧紧盘在头上的发。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十分精细。
大多练舞的人总穿大T恤和健美裤,而她却十分奇怪她在T恤外罩着一件肚兜,那时正流行肚兜,因此也并没什么十分诧异的。只是她的做得十分精细。
在9:30分我们有半个小时休息。从小便不是有多少伙伴的人,于是一个人在角落编手链子玩。
她也坐在角落,低着身子从包里拿出蛋糕,再掏出一副耳机,她看我盯着她,便晃了晃一只耳机,象是问我要不要听。
我走过去接了下来,她打开了线控,那是一个异常特别的男声,有别于平时常听的流行乐:
你对我说过你是执迷不悔,沉默地和我过着漫长的日子。
在那个寒冷的季节,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
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
我说不清听了那声音是什么感觉。“很干净的声音吧?那个女孩说道。我点点头,是啦!十分干净。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老狼的声音,那首歌叫作《只
有你陪我一起唱歌》。
两人那时都不是十分热情的人,于是,便无多少深交。最多见面打个招呼。
不过,那以后,每次休息时,都会与她一起听歌,她一直带着一个索尼的CD随声听,我一眼便看出,她是很有钱的孩子,像我们这样平凡的孩子根本买不起那样的奢侈品。
很可笑的是,我一直没有问她的名字。学舞的女孩大都这样,可以随便打弄,但也不问别人的姓名,不知是不愿,还是不屑,你知道,学舞的女孩总带有一些傲气。
日子渐渐久了,与她相处也久了,依然不是很热络的样子,只是知道有这个人,对她也不像对别人一般冷淡。
那时,她几乎次次排练都迟到,早餐带到排练厅来吃,我们的舞蹈老师每次对她剩在地上的蛋糕屑很是反感,而她总是不发一言地捡起来,再连同塑料袋一同扔进垃圾筒,她的表情十分平静。
我们就这样一人一只耳机地听歌,一些很干净很清澈的歌曲,带一种淡淡忧郁,很好听。阳光依稀照在她的脸上,毛孔很细,几乎看不出来,闭着眼,睫毛扇子一般合下来,默默无语。她的汗毛是金黄色的,聋聋的像小动物,有一种温和的感觉。
她的基本功不怎么好,大约身子太高,柔韧性还不如我,于是我曾经问她为何学舞,她顿一顿,然后回答,美体吧。声音自然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学舞的女孩,大都藏着一份梦想,有关展翅或者飞行的梦想,我是这样,其他人亦
然。
无事时,我爱观察她穿的各式各样的肚兜,什么颜色都有,但她大部分时间都爱一些内敛的颜色,深蓝、淡紫。
那些肚兜做得下了工夫,刺绣、缝纫,看得出都是手工制作的,那纤细的绣线在锦锻上绣满了花朵,一朵一朵弥漫开来,十分十分精美,也很繁杂。
她也曾告诉我,那些五花八门的肚兜的来历。
她们家族,只要是女孩,每年都要为她作一件肚兜,到了成年,刚好是十八件,是作为她的嫁妆压箱底的。
那么你就有十几件了?是啊。我们家的女孩都要学绣肚兜的,八岁之前是母亲帮着绣的。
她叫她的妈妈为母亲,这是一个带着生涩与疏远的称呼,我可以想象她所在的是一个多么大多么传统的家族,以至于都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一回家就搂着妈妈大叫“老娘,我回来了。”以至于与自己的母亲都得彬彬有礼。
这个沉默的女孩,总给我一种孤单的感觉。
那一次,舞蹈课完了以后下起了暴雨,我没有带伞于是一个人在学校里躲雨,直到雨停了才下了楼。
我在学校操场上看到了她。
操场上没有人,她的伞放在了地上,她在湿漉漉的水泥地板上翩翩起舞。
她的身形很修长,于是动作很优雅,但却因为基本功的原因显得有些僵硬,她伸长手臂,做出一个微微曲起的动作,她跳的是孔雀舞。
她很专心地跳着,一点一踏,一个手势,一
个亮相,手腕柔和,脚步轻盈,她仿佛会飞一样地跳着。
那是一种很渺茫的舞蹈,轻而美,好像是怕惊醒了什么,大概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她十分投入。
跳着,她终于停了下来,然后是最后一个台形,头转向右侧,一只手托在跨边,一只手擎到头顶,脚步是一点一踏,像是敦煌壁画的形象,她的脖颈露出来,象高傲的天鹅一般。
那一刻,我知道,她的确喜欢跳舞,要不然,必不能那么用心地跳。
是下午的课,直到夕阳把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我才想起离开。
那以后不久,再也不见她来上舞蹈课,在校园中也见不到了人,似乎蒸发了一样。问别人,都告诉我:“哦,那个女孩子呀,向学校申请了退学呢,好像要出国,哎呀!有钱人真是不一样,才小学呢,就出国……”,如此的回答突然让我愣住了,没想过她会离开。
于是想起了她最后给我听的那首歌,有这样的歌词:
月光下的城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早晨你来过留下过弥漫过樱花香,窗被打开过门开过人问我怎么说,你曾唱一样月光,曾陪我为落叶悲伤,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
我原以为我们没有什么纠葛,却没想到离了她就有那么多改变。比如开始喜欢她
以前给我听的那些清澈如水的歌,比如后来一直形容自己喜欢的声音为干净的声音,如此这般。
我真的以为,再也不会再见到她了。
那是元宵节,与爸妈一起去广场玩,想买一个灯笼玩,没想到在摊子前突然顿住了。是她!
淹没在一堆小摊小贩中,殷勤地问这个好不好,我知道她大约是不认识我了,可此刻我却更坚信是她。
虽然没有穿肚兜,虽然没有拿她那个很拉风的随声听,虽然并不是原来那么沉默,可是我认定了那是她。
那个弱小的,在一帮市侩中显得太特殊、太白净的女孩。
那一刹那,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走出人群,我不想知道她或她的家族经历了什么,背叛?失势?这些都不重要,只是她削瘦的样子让我微微有些悲哀。
仍记得她那些跳舞时高傲美好的样子。
仍记得她那些精美而意味长远的肚兜。
仍记得她十分爱在地板上划的那个“殇”字。
而今天,我知道,殇的意思是“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