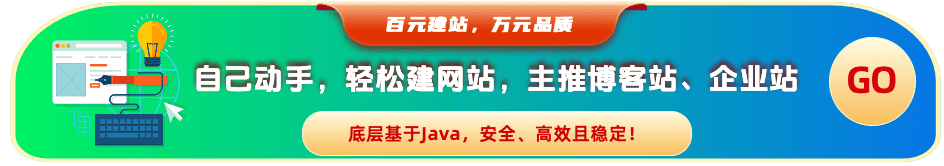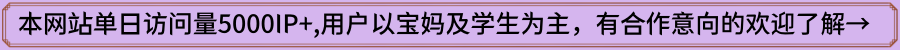老师,哥哥
谁都知道,班主任刘老师是我的哥哥。可是,要不是陪着玉霞同学正正经经在他家吃一顿饭,我还真不“认识”我这老师哥哥呢!
我与老师家是近邻。从一年级到发下四年级的新书,都是我这年轻的邻居哥哥在本村教的我。虽然在学校里喊老师,回家叫哥哥(母亲要我这样叫),但不管母亲为了啥事叫我到他家时,我总是推给妹妹—他毕竟是我的一个严厉的老师呀!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考上学走了。后来,老师快毕业了,我的大娘—老师的娘—却死了。我最怕死人,我再也不敢到他家去了。
老师毕业回来,分到这一所完小任六年级语文课,正巧,我也“考”进了这向往巳久的学校一这是“尖子”班呀!我发现,老师讲课比以前有板眼了,神情也比以前更严肃了,简直不见笑脸。
但在我的眼里,老师是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干什么都象课堂上那样畅通无阻,那样严肃而又自如,甚至不用吃饭都能活反正我看着是这样.
是的,我从前想象过老师可能要自己做饭,这回却真见到了。我和玉霞到他家的时候,他正煮胡萝卜,并且叫我俩也在他那里吃。我怎么肯?玉霞是到我家的客人,出于礼貌来坐坐的,何況煮的是胡萝卜,怎么吃?
老师切菜比我还不如,看他的汗吧。对了,我想起了老师的母亲,以前常到我家唠叨,说老师吃饭挺任性的。特别是考学那阵子,瓜干面煎饼一个也不肯吃,闹着光要糊粥喝;并且只要喝凉的,热了也闹。我不相信大娘的话。老师还“闹”?我都不闹了呀,再说老师复习功课尽在我们学校的饭堂里,他给我们上一阵课,似乎抱歉地默默回家吃饭了。糊粥可能是这样凉的吧?可能是不喝也得喝吧?但我知道大娘最疼她这最小的儿子的。据说,在寒假里,老师去开会学习期间,三天不回家她还想呢。
她常到我家说:“瘦了,瘦成啥样子了。半夜还不睡,我给他打个蚊子还吵我呢!嫌我不去睡.耽误他复习。”
老师终于考取了师范学校。乡下人都称他“大学生”。现在想来,考取师范也并不容易。但他只上了两年乱得与不上差不多的初中,全是自己钻的呀!
想来真叫人酸心:老师正临毕业实习的时候,我大娘死了。老师回家竞呜呜地哭起来,哭得要昏过去。我没见过老师、“大学生”还哭。我惊怕得跑回家去。
哦,老师也成了书上说的那种孤儿了吗?
……我拉着风箱,看着屋里迎门墙上挂着的大娘的大遗像,又似乎听到大娘以前在我家的唠叨。才几天呀,“闹”着吃饭的哥哥,今天闹谁去呢?我又看到了老师吃力切莱的手,脸上快要流下来的汗珠,老师今天怎么满面笑容呢?大娘去世后.他很少笑过,以前他星期天回家自己是不是也这样愉快呢?
呵呵,以前有大娘时他常是这样愉快的。那一次大娘走娘家回来—不知去了几天—从学校门前走过,老师竟跑出去扶着年纪不老却多病的大娘回家了.那亲昵的劲儿,惹得我们全偷着笑起来……
吃饭了。老师屋里的家具有些寒伧。似乎只有他的自行车是发亮的,值钱的,我知道这是个穷家底儿,房子也破了。西边的两间配房已打了半截墙,现在还“半截”在那儿。我又看了眼大娘的遗像,她那并不老态龙钟的眼神里似乎充满忧郁.我知道,那半截墙是地心血的结晶。我母亲有好几次眼泪汪汪地提到:那是大娘攒的鸡蛋钱买的石头打的墙。她满心想在老师毕业之前,盖好屋等儿子住,但事与愿违,过早去世了。记得过去,大娘曾问我:“你哥在学校是不是把钱都买好衣服穿了?”我说确实没见哥哥換很多衣服,两个褂子都不太新了,不是穿这件就是穿那件。“奇怪啊,他的钱尽买些什么呢?”我不知道老师挣多少钱。他在学校订了很多刊物。他看完后给我们轮着看的有《中学生》、《少年文艺》、《人民文学》什么的。他自己则常看些很厚的书,大部分是古诗词,再就是前阵子学生生病花了老师点钱,但都不知内情,以为学校报销吶!后来,才知道是花的老师的钱,就纷纷还给他。他却把钱还给个人叫我们自己去买书看!我那次头痛花他的几角钱,让我买了《唐诗一百首》和《写作一百例》。他说:几角钱对他无大用,同学们用了,作用就大了。
啊啊,钱的作用不一样?哦,听说国家要给老师长工资了,那时,老师的家里也许会好起来。
老师跟玉霞谈了些什么,我没太注意。老师拾掇碗的时候,我猛然看到他的左手指上缠的布条渗出血来。这是什么时候伤的?我怎么没看到呢?我赶紧替他去洗碗。他却说:“别别,停一会我刷吧”我鼻子一酸,赶紧背过脸去……
呵,后悔啊,我以前怎么就不到老师家来呢?怕“死人”吗?她不是慈样地被挂在墙上吗?怕烧火洗碗吗?根本没想过。哥哥在外当我的老师,作为他的学生、妹妹的我,就不该反过来帮他点忙吗?即使不是我的老师,作为邻居妹妹的我,就该敬而远之吗?若是索不相识的人……
啊,老师,哥哥!